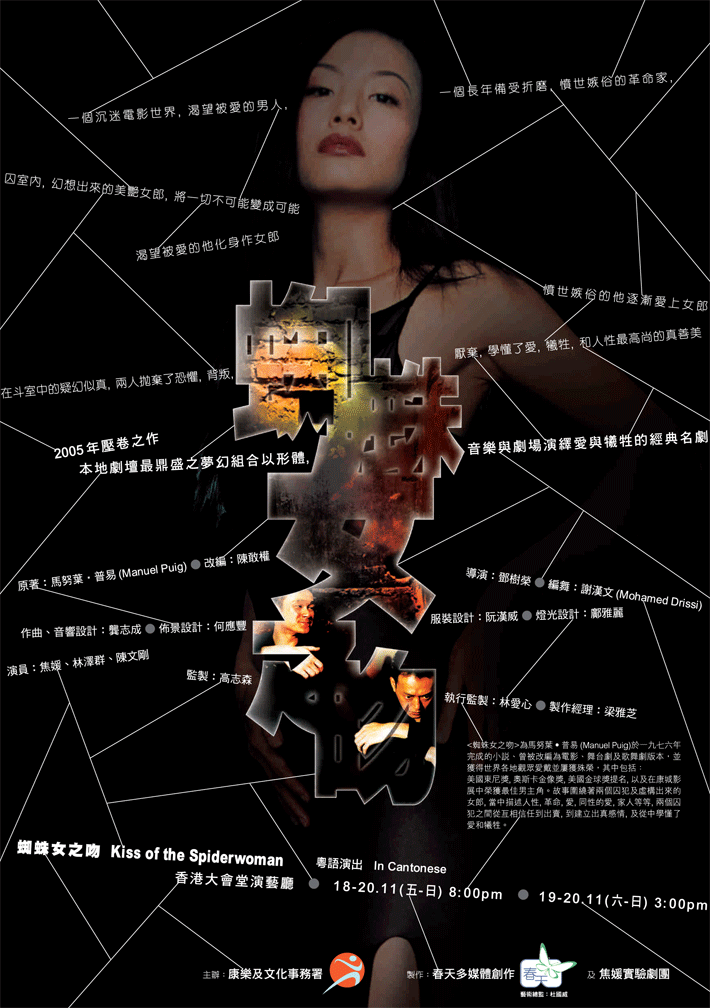不過,現代詮釋的神曲之路已不應該再是冒昧與啟蒙的鬥爭,而是在過份發展的現代性境況中,人性如何再一次擺脫由歷史創造的枷鎖。由港日台三地共同打造的《333神曲》,三位導演以個人想像來重現詮釋《神曲》中地獄、煉獄與天堂的意象,卸去了文藝復興前的人性理解,並將之化成三段直指現代的人性探索。
魏瑛娟說,她心目中的地獄是一種「暈眩」和「狂喜」的精神狀態。在由燭光圍成的演區之中,演員穿著沒有個性的小丑式西服,演繹著不同的片段:形式化的握手會面、無聊的手指遊戲、互相強行索吻等,這些都是滲透在現代社會中的人性表象,沒有內涵,亦毫無意義。它呈現出現代社會的地獄模樣,一種無個性、無意識的空洞狂喜狀態,人性進入了永劫回歸,重覆著無意識的具體活動,唯一可以指引路向的就只有套在白手套的手指,但從來沒有指清方向。於是,關於現代地獄的提問應該是:人既然不能創造出路,那麼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出路?最後,在一片榮光救贖之中,出路是有的,但晦暗不明。
「煉獄」,或者應該稱為「淨界」會更準確,提供了一條讓人洗滌罪孽,獲得救贖的路向。陳炳釗選取了一種較具神聖性的處理手法,重追但丁的煉獄旅程,並將之分成幾十段零散的言語片段,生成了一個受難者尋找救贖的序列。演區中的受難者背上被插上象徵十架的竹枝,以及《神曲》中但丁的精神支柱,女郎碧緹絲(Beatrice)的形象,於是受難者必須受著碧緹絲的精神引導,以其肉身飽嚐救贖路上的劫難。對受難者來說,救贖之旅在時間上是變動不定的,但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靈與肉之苦難鬥爭卻永恆地是唯一救贖的路,在文藝復興時代如是,在現代詮釋下亦如是。
雖然基督教教義中的天堂是一個永生的樂土,但劇場裡的天堂卻更加接近一種慾望高潮的狀態。人之大慾,有性慾、食慾和睡慾,在佐藤香聲的詮釋下,演員的大慾不斷地被充份滿足,不過這種滿足不是永恆的滿足,而亦是一種永劫回歸的過程:慾望不斷產生,又不斷獲得滿足。這種慾望產生與滿足的根源,並不是來自人性自身,而是源自天堂的蘋果。蘋果有著原罪的意象,但在劇場裡卻是一種「現代性的罪」,因為蘋果能滿足人之大慾,卻來源於現代社會,名牌、跨國企業、資本主義、全球化,全都在鮮紅色的旗布中顯現出來,這種「現代性的罪」化成挑起慾望的蘋果,讓人永遠活在慾望不能被充份滿足的狀態。如果說伊甸園的蘋果是上帝的陷阱,那麼現代性的蘋果就是現代社會的陷阱,令人泥足深陷。由此,在導演的眼光之下,「天堂」根本不是真正的永樂之土,而只是一個在煙霧和敲擊樂中的幻象。
當然,有一千個讀者(觀眾),就有一千種《神曲》。劇場的神曲之旅沒有真正救贖的終局,因為只有受難者以「肉身—主體」去親歷旅程,才能獲得救贖。藝術家為人們建構的救贖之路,只不過是一種很單純的選擇。
(原刊於此:【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