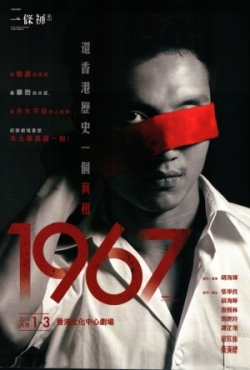不久前香港話劇團上演昆普寫於1997年的成名作 《安‧非她命》(Attempts on Her Life),劇中他借主角安(Anne)的缺席,直插戲劇本質的內核,拆解角色的主體存在,豪邁地示範了一場如何以戲劇顛覆戲劇的大戲。相對而言,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搬演的《城市一切如常》(The City)卻節制得多,昆普把他親手肢解的戲劇殘渣重新收拾回來,再砌成另一種戲劇情態。在這部寫於2008年的作品裡,昆普回到一個現代西方戲劇中屢見不鮮的命題: 中產階級生活的危機。劇中以客廳為場景, 一對中產階級夫婦如常生活,閒話家常,卻處處閃現出足令穩定生活旋即崩壞的火光。其設定大有法國新浪潮導演布紐爾(Luis Buñuel)的況味:中產階級生活是一個築夢過程,我們唯一在做的,就是不讓自己夢醒。
一向靈活多變的牛棚劇場突然被壓抑成一個當代歐陸劇場常見的客廳佈景,簡潔鮮亮、平靜、卻令人困窘不安。《城市一切如常》披著現實主義的外衣,劇裡臨摹了現實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但昆普出手不凡之處,在於他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把「現實」的本質問題化,質問「現實」(reality)與「真實」(real)之間的張力,如何構成中產階級生活的具體結構。如果說現實主義的戲劇精神是試圖以戲劇方法呈現出現實世界的內在秩序,那麼在《城市一切如常》裡,此內在秩序並非只有一種,而是三種。這三種秩序在戲劇情節的推展裡並排發展,既互相牽制,也互相吞噬,終使「現實」因受壓過度而爆煲。
第一種秩序是一對中產階級夫婦的日常生活。全劇五場,乃是順著時間發展,場與場之間相隔數月,每場皆有一些衝突,但情節上又無所累積,每場一過,下一場彷彿又回復正常。昆普巧妙地寫出了Chris 和Clair這對夫婦之間對話的日常性,既喋喋不休又沒頭沒腦,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著不著邊際的話。兩位演員張銘耀和黎玉清能夠壓下「演戲」的慣性,放鬆地把那種日常節奏演得絲絲入扣,恰到好處
然而,在一切如常的表象,第二種秩序卻如森林幽靈一樣在Chris 和Clair的生活中遊盪。中產階級生活的特徵是超級穩定,任何突如其來的事情,那怕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有可能破壞這種穩定結構。劇中最大的衝擊是鄰居Jenny突然闖入,「陌生人」往往是中產階級生活的爆破點,我們只要想想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的電影《瘋殺遊戲》 (Funny Games) ,就會明白在陌生鄰居身上所滲透出來的陣陣寒意。不過,《城市一切如常》中的Jenny卻從未破壞Chris 和Clair的生活,她反而是以一種超現實的方式,在他們的生活裡割開了一扇能窺見真實之窗。本來她只是來投訴孩子吵著她睡覺,卻無緣無故在他們 面前長篇大論地說了一個超現實故事:她的丈夫正在一個神秘城市裡參與一場神秘戰爭,故事內容血腥暴力,遠超夫婦二人所能理解的現實。我們不難從這個故事裡讀出對全球反恐戰爭的暗示,而夫婦二人也恰如其份地表達了典型中產階級對這類外界暴力的反應:事不關己,冷然以對。弔詭的是,這種現實世界的真實暴力卻是穩定生活本是虛假的鐵證,Jenny的故事看似超現實,實際上是比中產生活更現實的現實,只是Chris 和Clair不願意看而已。他們選擇把真實之窗適時關上,拒絕認識當代世界的殘酷,從而把夢境維持下去。
鄭綺釵在演繹Jenny時刻意保留著跟日常生活的一點距離,她的實感不及演夫婦的兩位演員,處處流露著一點份量輕微的怪異感,卻又不與夫婦的落差太大。而當Jenny說到那場遠方戰爭時,燈光和音效馬上變得詭異,大大催化了那種超現實氣氛,這顯然都是導演馮程程有意為之的調配。到了第四場,Chris 和Clair的女兒穿著跟Jenny一模一樣的護士服出場,以童稚之聲唸出充滿性暴力暗示的詩句,然後她跟Chris說出弟弟流血的情形,而Chris竟在她的褸袋裡發現血跡。這一切都似在暗示著一場沒有在舞台上出現過的家庭暴力,而最後卻竟又不了了之。對Chris來說,女兒的出場也是超現實的,她跟Jenny如孿生兒一般的形象,說明了她同是為割開那扇真實之窗而來的。於是,Jenny在第二場所說的戰爭暴力也顯得可疑了:暴力根本不在外面,而是隱藏在Chris的生活裡,卻被他以維持夢境為由而壓抑著 。女兒並未真正暴露真相,而我們唯一知道的,就是「中產階級日常生活之夢」的秩序,正漸漸被這些超現實的暗示蠶蝕至流出血水。
但全劇還有好一部份的情節,從未在舞台上發生過,而都是經由Chris和Clair的口中說出,這就是劇中的第三種秩序。從這些嘴巴裡的故事中,觀眾得知Chris的失業原因、他巧遇一個肉店工作的舊同學的經過,並且在酒吧裡遭到一名陌生女子所鄙視。另外Clair遇到一個曾經坐牢的作家,這個作家同跟女兒分開,後來他邀請Clair出埠參加研討會,最後他卻在酒店房間裡跟Clair懺悔。在最後一場的後設式結局尚未揭穿之前,這些在兩人口中說出來的故事似乎都是真的,Chris在第一場裡提及失業,第二場的確賦閒在家,而他後來也確實到了肉店工作;Clair一開始便帶回了作家送給她的日記簿,後來也確曾離家出埠。一切似毫無懸念,但這正是昆普機智之處:他們的如常生活沒有被破壞,並不代表他們的說話都是真的。在Chris和Clair的對話裡,我們隱隱聽到不少不合常理、可以追問下去的細節,像Chris的同事Bobby到底有沒有死,Clair為何不把作家趕出酒店房間,等等。這些細節上的不確定性可能來自錯誤記憶,也可能來自謊言,兩人對話並不完全理性,當中滿佈質問和懷疑,但兩人終也沒有深究下去。於是一種中產階級夫婦慣常的對話方式便躍然舞台,他們懷疑過,卻又不道破,故事真實性一直懸擱,一切再次如常,夢也繼續做下去。
法國精神分析大師拉康(Jacques Lacan)描述過一個構成主體意識的三角結構。想象界(imaginary order),前語言的欲望;象徵界(symbolic order),由語言構成的主體;以及真實界(the Real),不能言說的真實存在。拉康認為,我們日常對自我和世界的的認知,主要是在象徵界裡發生,那是由語言築構出來的穩定秩序。而在我們獲得語言之前的想象界裡,人的存在主要是建築於原初欲望,以及欲望無法得到缺失感,卻在語言世界裡被掩蓋著,我們可以叫自己堅信一切真實如故。可是,象徵界並非密不透風,我們有時會突然發現,生活並不如我們想象一般穩定,在表象底下,掩蓋著原來一切皆之虛妄的絕望真相。而我們之所以可以如常生活,往往是因為當我們偶而窺見這種虛妄,也總能及時叫自己視而不見。然而當生活的裂口愈來愈大,逼得我們不得不直面,象徵界的日常秩序就會馬上崩塌,真實界的荒漠也隨即顯現。
《城市一切如常》裡所描述的中產階級之夢,跟電影《盜夢空間》(Inception)裡的夢境結構其實有不少相似之處。在電影中,角色只有在兩種情況才會從夢中醒來,一是在夢中死亡,二是突然發現一些提示物,提示角色所見的夢中情境跟現實並不協調,如果角色堅持解釋的話,他便會發現自己正在發夢,他便會隨即醒來。《城市一切如常》裡的超現實符號(劇中第二種秩序)恰如夢境中不協調的東西,亦即是象徵界裡的裂口,在第一至第四場裡,裂口不斷出現,既衝擊著Chris 和Clair的正常生活,也挑戰著觀眾對劇中現實的理解。另一方面,即使Chris和Clair(以及觀眾)能一直維持對這場中產階級穩定生活的夢幻想像,他們兩人卻不斷遭遇到一些在現實上蠶蝕著其穩定生活的事情,例如經濟和工作上的困境、可能發生的外遇、又或者作家故事中所暗示,兒女對其人生來帶來的負累等。這些事情並未揭穿日常生活本是夢境的本質,卻不斷滋擾著他們的生活。中產階級生活起源我們對穩定富足生活的渴望,但在劇甫開始時,Chris 和Clair由就進入了中產生活的象徵界,忘記了這種對穩定生活的欲望是有可能無法得到滿足的(即想象界中的缺失感),上面提及的種種事情,無一例外地皆指向中產階級的焦慮感。然而,這些事情卻一直沒有完整地在舞台呈現,而只是借角色口中說出(即劇中第三種秩序),這似乎暗示著,焦慮感既來自現實發生的事,也來自角色的憂慮。而昆普的猛招,正是故意將第二和第三種秩序同時鑲嵌在Chris 和Clair的生活裡,於是他們對中產生活的懷疑,跟對現實世界的懷疑也糾纏在一起,而成為如常生活底下的深層結構。
因此,第五場便恍如阿歷山大大帝斬開戈耳迪之結(Gordian knot),將一切疑惑和懸念盡行解拆、展開。戲中的兩份聖誕禮物恰如這場中產階級之夢的提示物,Jenny送的刀子暗示了如常生活底下的所有暴力,而Clair的日記簿則是驚破夢境的最大關鍵。如今導演馮程程以頗重的手法把夢的裂口扳開,舞台的呈現愈見詭譎,飾演Chris的張銘耀漸漸走向精神崩潰的邊沿,而飾演Clair的黎玉清卻全然把情緒壓下,跟張銘耀形成鮮明的對立。於是前四場的糾結模糊也突然真相大白了:Chris的全部都生活是虛構的,他成了此夢的唯一主體,在日記簿上的故事裡,他看見了自己的真實界,夢突然被驚破,他終於發現,自己並不存在。
可是,即使昆普構思出這樣一個爆炸性的後設終局,在字裡行間,他仍殘留著一些曖昧的東西。在最後一段裡,當Chris讀罷日記簿上的故事,他問Clair:「我是虛構的嗎?」而Clair的回答卻是:「跟我一樣。」在此,昆普保留了最後的一個懸念:這是誰的夢?是Chris的夢?還是Chris和Clair兩人的夢?昆普一方面要表現中產階級生活的虛幻性,同時又以相同的解夢方式拆解對劇場現實的既有想像; Clair未必是最終的築夢者,她或許是夢境的一部份。而作為劇作家的昆普,始終隱身於文本背後,而沒有像諸如《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這類後設劇作那樣,在舞台上坦露出創作者與角色之間的張力。事實上,全劇終結於故事裡的中產生活跟戲劇現實的雙重崩塌,但崩塌後留下的卻不是絕對虛幻,也不是大他者(the Other)的微笑,而是虛實之間的曖昧模糊。單從文本上看,結局是留白了,昆普僅拋下一個問題:在這個文本裡,什麼才是真實?然後就飄然而去。而我們所看到的,卻是一個令人無法直視,也無法解通的「真實界」。
《城市一切如常》對導演的最大挑戰,並不是如何回答劇作家的問題,而是必須在「回答」和「不回答」之間作出抉擇。馮程程選擇接下問題,並花了最大的努力「回答」。她成了戲的解夢師,她將Chris放在夢境中心,讓Clair稍微逸出夢境外,變成Chris之夢的終極提示物。Clair也成了壓倒第四堵牆的最後一根蘆葦,在她之後,戲劇之夢亦告完全倒塌。
觀眾必須帶著透不過氣的胸臆離開劇場,他們都以為看穿一切。但我並未因此而滿足,夢都解透,懸念沒了,我也只好清醒過來。
(原刊於此:【link】)